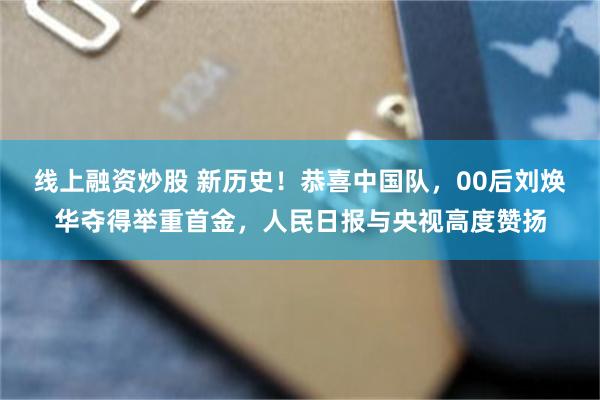屈原到过邯郸吗?股票的交易平台
□宋涟圭
屈原,芈姓,屈氏,名平,字原,战国时期楚国人,伟大的浪漫主义爱国诗人,受楚怀王信任时曾任左徒等职,兼管内政外交大事,力主联齐抗秦,前278年楚国郢都被秦军攻破后,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国。他似乎与同时代的赵都邯郸没有什么关系,《史记》等众多典籍中没有相关记载,他自己的作品中也无任何反映。
但是,如果我们暂时抛开他诗歌的成就,重点审视他楚国大臣、政治家、外交家的身份,再去检阅史籍,就会发现“屈原到过邯郸吗”这个问题并不是空穴来风,答案也许就隐藏在许多蛛丝马迹之中。
《史记·赵世家》载:赵武灵王“十三年,秦拔我蔺,虏将军赵庄。楚、魏王来,过邯郸”。这一年也是楚怀王十六年、周赧王二年,即前313年。
是什么外交大事使楚、赵、魏三国君主会聚邯郸呢?这还要从五年前的山东六国合纵抗秦说起。《史记·楚世家》载:楚怀王“十一年(前318年),苏秦约从(纵)山东六国共攻秦,楚怀王为从(纵)长。至函谷关,秦出兵击六国,六国兵皆引而归,齐独后”。对于此事,《史记·六国年表》则只说“五国共击秦,不胜而归”,齐国未出兵,也没有说是苏秦约纵。看来太史公在此事上的表述是自相矛盾的,也许是心有疑虑吧。1973年底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保存了苏秦的书信和游说辞十六章,所载与《史记·苏秦列传》不同,证明了这一怀疑是有道理的。
展开剩余80%苏秦(?—前284年),战国时期纵横家、外交家、谋略家,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燕昭王于前311年即位后,为报齐仇而广招人才时,苏秦才投奔其门下并得到重用,从而登上政治舞台。他一生主要为谋求燕国强大、防齐吞并,而运用让齐“西劳于宋,南罢(疲)于楚”的策略,奔波于齐、赵、韩、魏等国间,组织合纵攻齐或合纵攻秦。因此,苏秦不可能也不会参与前318年的六国合纵抗秦之事。
那么,究竟是谁促成了这次六国合纵抗秦的事呢?
是屈原。这有史籍为证。汉刘向《新序·节士上》载:“秦欲吞灭诸侯,并兼天下。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从时间上看,这件事应发生在前319年。当时屈原得到了楚怀王的重用,任左徒,是一个仅低于令尹的高阶职位,兼理内政外交。他“博闻强记,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史记·屈原列传》)。因此,楚怀王会把这么重要的外交大事交给他去办,而“以结强党”就是要结成强大的六国联盟。这次出使,屈原不会只到过齐国,还应奔走于赵、韩、魏、燕之间。这才有当年齐、楚、燕、赵、韩助公孙衍为魏相,行合纵之策,结成六国联盟;也才有第二年(前318年)公孙衍发五国之兵攻秦,即《史记·六国年表》所说“五国共击秦”。这应该是屈原第一次到赵国来邯郸。
但是,六国联盟第一次联手出兵攻秦,结果却是“不胜而归”。这恐怕不是军力上秦强而六国弱可以解释的。不胜而归不是战败(《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云“战败”,不知何据)而退,这说明“齐独后”,未能与秦军接战,而其余五国军队一见秦军就分崩离析了。其深层次的原因恐怕是屈原的合纵工作并没有使六国的思想认识统一到合纵抗秦大业上来,六国各有小九九而形不成合力。
此后五年,一方面“秦患(六国合纵)之,使张仪之楚,货楚贵臣……共谮屈原。屈原遂放于外(贬谪为只管王族事务的三闾大夫),乃作离骚”(刘向《新序·节士上》)。楚怀王中了张仪的离间计,徒为纵长。另一方面,秦、齐与韩、赵、魏间战事不断。据《史记·六国年表》载,仅第二年(前317年),“(赵)与韩、魏击秦”,“秦与韩、魏战,斩首八万”,“齐败魏、赵观泽”。其中,赵受秦害最烈,此后连年“秦取我中都、西阳(安邑)”,“秦败我将军英”,“秦拔我蔺,虏将赵庄”。因此,赵谋抗秦也最着力。于是赵武灵王想起了五年前屈原的合纵之策,便邀请当时的合纵长楚怀王和近邻魏哀王,一起来到赵都邯郸共商抗秦大计,也就顺理成章了。这时,韩已受秦控制,齐与赵、魏有隙,燕尚无君,故未受邀约。而在楚国,“是时,怀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以至于此。于是复用屈原”(刘向《新序·节士上》)。这时,屈原的职务是三闾大夫,楚怀王正要派他出使齐国,以修复关系。接到赵武灵王的邀请后,因为这是一件涉及合纵抗秦的多边外交大事,屈原原本就是这一政策的提出者和实施人,因此楚怀王就让屈原陪同上路了。他们先到魏都大梁,约了魏哀王一起到邯郸赴邀。邯郸之会商毕,楚怀王先行回国,而屈原按原计划使齐,促楚、齐重归旧好。另外,从屈原两年后才归国的情况看,他此行还应到访过韩国等地,为恢复合纵抗秦的局面而奔走。这应是屈原第二次到邯郸。
然而,未等屈原归国,消息已传到秦国。“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张仪免相,使张仪南见楚王”。张仪谎称让怀王“使使者从仪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让其“闭关而绝齐”。“怀王大悦,乃置相玺于张仪”,不听陈轸劝告,宣言绝齐并“使勇士宋遗北辱齐王”(《史记·楚世家》)。就这样,导致楚国既“绝强齐之大辅”(刘向《新序·节士上》),又一寸土地也没有得到。于是,怀王大怒,举兵伐秦,大战者数。秦兵大败楚师,斩首数万级。楚国还丢了汉中之郡,元气大伤。同时,因楚绝齐故,齐转而连秦,当韩、魏乘机袭楚时也不予救。两年之后,“秦使人愿以(原被秦掠夺去的)汉中地谢。怀王不听,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刘向《新序·节士上》)。但是,张仪“至楚,楚囚之。上官大夫之属共言之王,王归之”。“屈原使齐还,闻张仪已去,大为王言张仪之罪。怀王使人追之不及”。屈原与赵武灵王的合纵抗秦努力又一次化为泡影。“后秦嫁女于楚,与怀王欢。为(秦约怀王)蓝田之会,屈原以为秦不可信,愿勿会。群臣皆以为可会。怀王遂会,果见囚拘,客死于秦,为天下笑”。
楚怀王“为天下笑”者,岂止“客死于秦”。这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史记·六国年表》等载,前297年,“楚怀王亡来(赵),弗内(纳)”。这一年是赵惠文王二年,也是楚顷襄王二年,楚怀王被秦囚拘的第三年。为什么赵不纳呢?《史记·楚世家》说,楚怀王逃出秦牢,“走赵以求归。赵主父(武灵王)在代,其子惠(文)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恐怕赵惠文王不仅仅是由于恐秦而不敢借道,更是因为楚怀王反复无常、两次破坏主父与屈原的合纵抗秦大业而鄙弃他。
由此可见,屈原一生中不仅到过邯郸,而且不止一次。那么,为什么司马迁只记“楚、魏王来,过邯郸”和屈原第二次使齐呢?笔者认为有三个原因。一是他既已把第一次合纵攻秦事误记在苏秦名下(虽然有疑虑),当然不会再去考虑屈原的事了。他可能未见过《汉书·艺文志》中所列的纵横家书《苏子》三十一篇,也未见过保存了苏秦书信和游说辞十六章的《战国纵横家书》。二是第二次去邯郸时,屈原只是楚怀王的随从,也许司马迁认为有王在自然略记臣事。至于记第二次使齐事,是因为司马迁认为事关楚国命运,既可表现楚怀王的昏庸和信馋,又可写出屈原的忠贞和睿智。三是司马迁跟现在大多数人一样,把屈原主要看作诗人,而不是政治家、外交家。这从《史记·屈原列传》的篇幅、布局就可看出来:大约三分之二的篇章是介绍和评述《离骚》等诗作的。而刘向的《新序·节士上》与此相反,屈原之章几乎全篇都写其为政与外交,对诗作反而一笔带过,把屈原看成政治家、外交家,虽然篇幅不长,却留下了宝贵史料。
屈原像
来 源: 《赵都文化》杂志
编 辑:张禹 冀翔
审 核:孟庆文
投稿信箱:hd2926@163.com股票的交易平台
发布于:北京市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在线配资炒股平台网_在线配资炒股开户_在线配资炒股交易观点